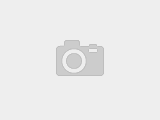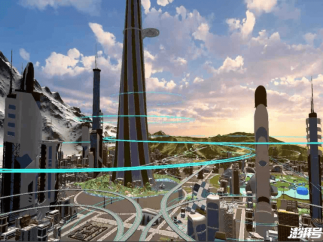知春路希格玛大厦,五道口清华科技园启迪大厦,从北京地图上看,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只有3.1公里,但张亚勤从希格玛走到启迪大厦,用了23年。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1998年底,32岁的张亚勤回国与李开复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希格玛大厦成为他第一个办公场所。张亚勤向记者回忆,“那时候我需要和李开复证明在中国可以做出一个顶尖级研究院,对我们来说,最难的还是人,要找到顶尖级科学家愿意回来。”
希格玛这栋7层高的驼色小楼见证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从0到1的成长。“包括后来陆续回来的张宏江,沈向洋,郭百宁,马维英,林斌,王坚,李世鹏,朱文武,汤晓鸥这些人,他们回来后,至少可以继续同步美国的那个水平。另外我们又找到一批最优秀的年轻人,像张黔,吴枫,童欣,王海峰等,刚从学校毕业就加盟了。”张亚勤回忆。

张亚勤在希格玛度过了5年,期间,微软中国研究院升格成微软亚洲研究院,张亚勤成为首任院长。这5年,微软亚洲研究院网罗了50名世界一流研究员和120名国内顶尖人才。希格玛当时也被戏称为全国智商密度最高的建筑。2004年,38岁的张亚勤晋升微软全球副总裁,成为比尔·盖茨智囊团核心成员。
时随势易,微软亚洲研究院后来成为中国IT互联网产业的黄埔军校。有这样一份名单在产业界流传:字节跳动的张一鸣2008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并在此认识了马维英和李航,后来马维英字节AI实验室的负责人,李航也加盟了字节的AI实验室;他们都与张亚勤共事11年。还有小米的联合创始人林斌,他2001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
此外,微软亚洲研究院还向业界输出了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骨干:最近即将上市的商汤科技,创始人唐晓鸥,CEO徐立,联合创始人杨帆都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或长或短的工作过,还有旷视科技、依图科技负责人等等。
张亚勤48岁出任百度总裁,5年后从百度“退休”。2020年7月加入清华大学担任智能科学讲席教授,并筹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
张亚勤把AIR的地址选在了清华东南门的五道口清华科技园。AIR成立这一年,张亚勤的工作分三块,招人,定方向,资源。对张亚勤来讲,他的挑战是AIR能不能成为顶尖级研究院,其衡量因素是能不能做出颠覆性的重要科研成果。
通常早晨九点,张亚勤会出现AIR的办公室。近一段时间,张亚勤在比较系统的看生物学的书籍。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Lewin基因XII》,还有一本《肿瘤转化研究与免疫疗法》。张亚勤说,家里还有更多类似的书籍,车上也有,看得比较慢,慢的原因是他同时还要做智慧交通领域的研究。
张亚勤喜欢做从零到一的事情,微软研究院如此,AIR亦是如此。现在,张亚勤不需要证明中国能不能出顶尖级研究院了,国内很多学校和机构,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因此,张亚勤有信心AIR在未来能有重要影响力。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AIR所在的清华科技园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如今的清华科技园,东起清华南路,西至蓝旗营高校教师住宅区,南邻成府路,北至清华大学南校墙,占地面积 25 公顷、建筑面积约 73 万平方米。这片土地的价值曾被这样描述:四百多家企业,包括搜狐、网易、还有后来的快手。清华科技园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对张亚勤来说,他的身份在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变换,但科学家这个标签一直未曾改变。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那些年,他曾向女儿这样介绍他的工作,“家里用的很多东西,包括高画质电视(HDTV),DVD光碟机,电脑的操作系统Windows,打网络电话及收发Email等,都有爸爸的专利。”在百度,张亚勤则专注于自动驾驶、云计算、量子计算、芯片等AI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而在AIR,张亚勤和他的同事们专注于智慧交通(AI+Transportaion),智慧医疗(AI+Healthcare)+智慧物联(AI+IoT)三个方向。
2021年11月18日,张亚勤当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外籍院士。张亚勤表示,“这些年来,对技术的热情,学新东西是我一直坚持的。”
回归高校一年半后,张亚勤近日接受记者专访,系统阐述了对元宇宙、AI与生物科学、自动驾驶和智慧物联等技术领域的思考。以下为记者整理的专访实录:
元宇宙不是另一个虚拟宇宙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大热的元宇宙?
张亚勤:元宇宙是真实社会、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是大趋势,包括像AR、VR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我是认同的。但在我看来叫元空间更好一点。目前很多技术的发展还需要时间,比如VR/AR眼镜,我们可能需要达到三千个(PPI)才能真实地(呈现)内容,比如眩晕问题,定位问题,显示问题,包括高通量低时延通讯网络也需要一些时间,还有就是“元宇宙”的需要内容生态。
目前推动元宇宙的大企业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因此,元宇宙的定义也不清晰。例如,Facebook收购了Oculus后,把过去的AR、VR加上新的内容,讲了几个不同的维度(的内容),我觉得都有道理,等于他产品的升级。而做游戏的公司,这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的升级版。微软的Teams,一款会议通讯软件,已经做了十多年了,上个月,微软宣布Mesh元宇宙就是teams加上更好的Avatar新功能。英伟达提供基础GPU算力,元宇宙是新的机遇。从技术方向来讲,大家都在按照自己的思路和计划发展对元宇宙的定义也不一致。
第二点,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我认为一定是真实世界是根本,虚拟世界是我们的一个延伸。而不是相反的,或者是等同的。我不希望我们人类生活在完全虚拟的空间里面。我们真实世界的人,玩游戏可以,完全虚幻世界也可以,但那只是你的一部分,是一种体验,且是一个小部分,我们不能一直在玩游戏,我们的身体,思维,以及生活,工作和社交方式还是要建立在真实世界里。
第三个是现在看到的,有很多公司,利用“元宇宙”概念炒作。现在元宇宙卖房地产,卖(NFT),卖货币。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目前有不少炒元宇宙概念的人,并不是真正做事情的人,其中投机者很多。这要说自己是元宇宙公司,股票马上就疯涨,这很危险,不要炒作。
对待元宇宙,我们要用开放的态度,但有些人讲元宇宙完全是胡扯,我觉得这个也要避免,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元宇宙。
我更喜欢“元空间”这个名字,是扩充我们真实世界的新空间 而不是另外一个虚拟宇宙。
自动驾驶会成为万亿级赛道
记者:智慧交通(AI+Transportaion)会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张亚勤:AI本身是一个工具,你可以想像10年、20年之后自动驾驶的车里面不需要司机,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你可以用手机APP或者语音告诉车你要去的地方,中途所有的路径都是经过算法优化的,整个交通的堵塞会大大减少,排放会大幅度降低。最重要的一点,自动驾驶会挽救生命。现在90%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喝酒、疲劳、看手机等,有了无人驾驶之后车祸会降低一个数量级。总的来说,自动驾驶第一是安全,第二是高效,第三很环保,第四是一个大的产业机遇。

记者:自动驾驶会成为一个万亿级赛道吗?
张亚勤:对,我在百度工作时曾和麦肯锡一起做了一个分析,预计到2030年整个自动驾驶产业会新增1.5万亿美金的市场,现在车辆的市场是3.5万亿美金,不包括交通细分市场。汽车这个产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无人驾驶、软件、电池其实对这个产业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我们以前叫四化,特别是智能化无人驾驶,是颠覆最大的一个,这个颠覆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大的机会。
记者:技术把起点拉平了是吗?
张亚勤:对。过去100年主要是欧美企业在做的燃油机,知识产权也好,技术也好,产业链也好,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们成为跟随者。现在,整个产业技术的基本要素发生了变化,我们有机会颠覆和超越欧美,且可以挽救生命,降低排放,让城市更高效。既有社会价值,又有产业机遇。
记者:现在有的企业做飞行车,这是一种概念还是说在某一天会实现?
张亚勤:这个都会实现,其实是一个无人系统,可以是车,可以在天上飞的,也可以在海上航行。有了无人驾驶技术,未来在规划城市的时候,就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记者:真正的无人驾驶落地大概还要多久?
张亚勤:无人驾驶变成现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技术一直在进步,比如现在亦庄有几十辆的无人车里可以实现“无人”了,过去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安全员坐在车里。在目前这种有限制的环境下,无人车的水平已经和人开车的水平差不多了,11月国家已经同意无人驾驶可以商用,过去试乘是不付钱的,现在在那70平方公里范围内,要付费了,这是无人驾驶车走向商业化了。
无人驾驶国家在政策支持的力度很大,在北京、广州、长沙,城市推广的幅度很大,但政府也很谨慎,这是关乎人的生命的。目前百度差不多跑了2000万公里,一直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人员伤亡。只有安全无人驾驶才能慢慢落地,不能急。汽车产业和别的产业不一样,产业周期很长,比如电动车,到目前为止至少发展20年了,直到去年电动车出货量第一次超过10%。回到自动驾驶,无人车、和无人系统都是智慧交通很重要的一环。
打通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
记者:智慧医疗(AI+Healthcare)在未来会给产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张亚勤:以新药研发为例,目前要发明一个新药需要差不多12到15年时间,需要10到20亿美金的费用,周期很长,造价很高。AI的出现,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把这个周期缩短很多。
这里面有几个大的趋势,现在整个生物世界在数字化,我以前一直讲物理世界在数字化,生物世界也在数字化,蛋白质、基因、细胞都能用数字的方式表示出来,数字化的好处是有大量的数据,加上很强的算力和算法,人工智能里面这么多年技术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目前很多制药很多是在小分子找精准靶点,现在我们把它用到大分子,抗体,以及TCR个性化的疫苗和药物,还有最近AlphaFold在蛋白质解析方面的进展等等。
另外就是基因编辑,这个是兰艳艳教授带领学生完成的,基因有编码区和非编码区。编辑的基底清楚之后,AI算法就可以更精准的预测基因序列变化,同时靶点也更加的准确。因为AI能更快地找到规律,减少搜索的空间,速度更快。
另外是干实验和湿实验可以闭环,湿实验就是真正的生物实验,生物世界数字化后,有了AI的助力,马维英老师还有彭健他们设计把湿实验和干实验完全形成一个闭环。干实验讲的是AI算法,湿实验就是纯生物化学实验,把AI加到湿实验里就能完全加速实验周期,就像AlphaGo下围棋,最后人没法跟它下,它等于是左右手互相下,其效率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也在研究打通干湿实验,形成闭环,我们做基因编辑,新药研制等都可以运用。
谷歌AlphaFold通过基因序列预测蛋白质结构,而AlphaFold2彻底改变了蛋白质从氨基酸序列到三维结构到功能的研究。过去这些年,科学家们用冷冻电镜和高精度X-ray在找蛋白质结构,AlphaFold2出来之后就把这个工作指数性的加速。我们希望AlphaFold能够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基石,能够运用到别的地方去。

记者: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这两个领域打通容易吗?
张亚勤:做计算机的人,做人工智能的人和做生物生命科学的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这两个领域一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也好,使用的体系也好,方式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两个领域打通,我们把这叫做破壁计划。
第一次把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用到蛋白质三维结构解析的,是芝加哥丰田实验室的许锦波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彭健等,他们现在都是清华AIR的访问教授,就坐在我旁边的办公室。AIR的生物计算团队由马维英教授带领,有兰艳艳教授和近10位年轻的科学家们,是一个很强的团队。
记者:这个团队最近在忙什么?
张亚勤:彭健教授团队最近做的HelixonAI 在全球持续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CAMEO(Continous Automated Model EvaluatiOn)上,刷新了AlphaFold2的记录。
同时,他们最近在新冠抗体方面有新的进展,还发布了全球首个由AI设计的新冠抗体,可以广谱的适用于最新的变株。
智慧物联降低5G和数据中心能耗
记者:智慧物联(AI+IoT)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改变?
张亚勤:首先有很多用处,IoT这个领域分得太细,而且比较杂,大家开始讲物联网,家庭里面的物联网,产业里面的物联网,我们现在把物联网用到双碳,用到节能,如何减少排放。我跟我们AIR的科学家讲,先把大型的数据中心包括人工智能算法大模型的排放解决掉,如果能把数据中心的排放只减少10%就有很大的成效。
我们近期的一个工作是5G基站,5G用的Massive MIMO里面有很多基站,我们最近做的一些工作,是真实的基站加上一些模拟的场景,用多Multi-agent cooperative Contextual Bandits这个算法,也包括一些离线的深度学习算法,使得功耗降低了15%左右、5G网络覆盖质量提高了5%左右。
还有一点是现在把它用到各种能源的融合上,太阳能、风能、水能,还有氢能。我们并不是做能源本身的,但是由于有AIoT,第一可以知道能源本身的效率,包括什么时候合、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存,也知道它们的排放,用大量数据,用AI的算法去做这个优化。
另外詹仙园教授做的发电系统,比如火电,可以通过强化学习算法去做数据分析、决策和控制。初步结果显示,可以提高火力发电机组的锅炉燃烧效率,如600兆瓦的机组,每年可节煤3-4千吨。如果更多推广的这样算法,发电机组就会有更多的节省。
记者:还有别的用途吗?具体形式是什么样的?
张亚勤:其实AI可以用到很多地方,赵峰教授和刘云新教授负责这个方向。如何让技术做这种在手机上运行的小模型,它的效果也是从大模型里边提取出来,用边缘计算的方式能不能把这些能耗降下去。通过新的算法模型量化、压缩,面向异构进行模型生成,边缘端可以达到80%、90%的性能,同时算力减少几十上百倍。
记者:这三个方向这一年进展怎么样?
张亚勤:智慧交通也好,智慧医疗,还有智慧物联,这三个方向对社会,对产业有重大影响,也和AIR的科学家们背景比较一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三个方向,这一年确实有蛮多进展,虽不能说是突破性的,但也是有一些阶段性的进展。我觉得只要方向对了,人找对了,就要看看三年或者五年后的发展。
高校创新和企业创新的差异
记者: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也在Sarnoff研究院工作过,现在回归高校。在您看来,高校创新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张亚勤:大部分企业的研究院,是为企业战略服务的,企业研究院的成果基本都服务于企业产品。企业研究的优势:第一是资金和资源相对比较稳定。第二是有组织的,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共同奋斗,由资深科学家带的团队,氛围轻松。相对局限在于研究成果仅用于本企业地战略和产品,当然这对于企业的性质是无可厚非的;还有一点是企业产品研究的周期比较短,三五年相对都是比较长线的研究,一到两年是常态。
记者:高校创新有什么不同?
张亚勤:高校的很多研究是属于好奇心驱使的。我作为一个教授,有学生资源,对一个问题有兴趣,然后就去做这个事。高校创新与企业创新相比优点是:其一开放性,其二可以长期解决一些很根本的科学问题,研究没有任何限制。从全球来看,大学的基础研究对整个社会是有巨大贡献的,很多科学的重大的成果都是大学教授做的。高校创新相对系统性比较弱。总的说来,高校创新和企业创新各有优势。
记者:高校创新和企业创新之间的互动是什么?
张亚勤:在美国30年前,很多大型企业研究院真正做长期的基础研究。 比如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和无线通信等基础技术,施乐研究院发明互联网和图形用户界面,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现在这种机构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研究越来越产品化,美国的大企业也有这个趋势。目前做基础研究的就只有微软等少数企业了
记者:这些年大企业的理想在变少?
张亚勤:对。这是美国这三十年的一个变化。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企业原来没有研究院,现在开始有企业研究院了。有了之后,开始考虑长期的问题。所以企业和学校是两个极端,每一个都有它的作用,都是很好的机制,没有谁好谁不好。比如深度学习,最基础核心的算法是学校的教授做出来的,但到了比如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才变成主流。
记者:AIR的很多科学家都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也有研究院的经历,这意味着AIR既会保留高校创新的基因,又距离企业一线不会那么远?
张亚勤:AIR做的东西是相对有组织的,但组织不像企业那么严密。比如说我们每个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有自己的工作计划,他自己也有PI(学术带头人),但是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不是经理和员工关系,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方向和团队。大家为了一个大的战略和方向去合作。尽管AIR的资金主要是从企业来,但是并不需要给企业做产品,我们希望保留高校创新的某种自由基因,但又希望能做些有组织的系统工程
记者:所谓的无用的研究会带来什么?
张亚勤:高校的很多研究,当下看起来确实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去解决,这个也很重要。没准将来技术上的颠覆式创新就来自于这种无用的研究。我觉得科研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和形态。不同的维度,不能讲这个就比那个好,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各种形态。而关于AIR,我想探索一个新的模式。
AIR要做出颠覆性的技术
记者:AIR建院一周年,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与当时建立微软亚洲研究院有什么不同?
张亚勤:第一是招人,每个人来的人我都要聊很多次;第二是定方向,第三是找资源。1999年我和李开复一起要证明在中国,能做出一个顶尖级的研究院。现在AIR不需要证明这个问题了,国内很多学校、机构都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现在中国的科研环境,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较之前有大幅度提高的,和20年前完全不一样,因此成立AIR,我是信心大增的。
但AIR能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研究院还是需要我们去证明的。能不能真正做出有颠覆性、很重要的科研成果。多年后,我希望在国际范围内人们谈到AIR,能想起来哪些是AIR做的。我们AIR已经有了很好的科学家,也有一些不错的研究基础,做成的几率很大。前天研究院一周年,让我讲话。我讲了几点,第一要要有梦想,而且这个梦要大要远。第二要把事做实了,代码是一行行写出来的,文章是一篇篇发表的,安安静静的把事情做实了。第三做人要正。

记者:需要给科学家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氛围?
张亚勤:人要正,文化来讲还是要简单。科研人员态度和品性要好,平时大家在一起,要与人为善,要善待同事、善待学生、善待老师,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大家来AIR工作,一心放在工作上,办公室政治这种东西,我是不能容忍的,做事快点、慢点没关系;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婉转,有的人直接,有人内敛,有人张扬,这些都没关系,但有一点绝对不能使坏,这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
记者:研究院的资金来源于哪里?
张亚勤:主要是企业。也会承担一些国家科研项目。
记者:AIR研究院和企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张亚勤:在AIR的三大方向上,企业的合作伙伴有需求,我们能帮它解决问题,而不是企业有这个需要,AIR帮他做个项目,不是这样的。AIR的研究成果及用户资源都是开源的,数据集也是开放的。我们刚刚发布了几个开放的数据集,企业必须要认同这种做法,不是说合作成果就是企业独家的。合作企业也是很清楚,大部分科研成果不是为目前产品的,也许下一代,也许下下一代。如果合作企业说现在产品马上要用,或者觉得他们人手不够,让AIR帮找点学生,那找错地方了,我们做的东西是面向未来的。但我们也需要和企业合作,企业有大量的沉淀数据和场景。比如车,车需要大量的数据场景,百度将近两千辆L4车在地面上跑,这些数据大学是没有的,只有基于真实的数据研究出来的东西才可以验证研究成果的好坏。
做教育,要让人变得更真,而不是更假
记者:科学家、企业家和老师这三重身份,你更喜欢哪一个?
张亚勤:其实我没怎么想过,更喜欢老师这个身份吧。
记者:您母亲也是教育工作者,她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张亚勤:母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除了母亲,还有祖母。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小时候说谎了,绝对会受到最严重的惩罚。做错事没关系,但绝对不能说谎,从小就这样。我母亲不太管我,我12岁去合肥上大学,从太原到合肥,我母亲都没有送我,送到太原火车站就走了,后来连火车站都不送了,直接送到汽车站。
记者:您母亲很智慧,懂得放手。您如何教育您的孩子?
张亚勤:我觉得我母亲比较懒(笑)。我也管的很少,我们家庭有一个微信群,每天在群里都有沟通,氛围很好。
记者:您认为教育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
张亚勤:第一点我觉得是真。第二点要独立,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一点是要创新,要有一些创新的能力。
记者:现在您也带博士生,您教学生的理念是什么?
张亚勤:教育首先是要真,要真实,要诚实,教育人要真。第二点,教育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他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随波逐流。第三,要有再学习的能力。现在的世界变化很快,培养学生做博士论文,最后那个论文也许就没用了,他学的知识也没用了,但最后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通过再学习,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怎么利用最短的时间学习新东西,然后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三点很重要,我希望我的学生们永远保持纯真。
总的说来,做研究也好,做教育,要让人变得更真,而不是更假。我喜欢淳朴的学生,不喜欢过度包装自己的学生。
记者:您如何看待教育产业当下的一个现状?
张亚勤:我觉得学生们把很多的时间放到应试教育中,这个是很危险的。我那个时候就是高考的时候很辛苦,上了大学也没那么辛苦,中学也没那么辛苦。现在有很多的考试,各种补习,都是为了各种各样的证书和帽子,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为了帽子和短期评估,很难做出大成绩。真正做研究的人要耐得住寂寞,有韧性。包括深度学习的算法和mRNA 早期主流的期刊都不刊登。幸运的是现在整个大环境已经在改变了。
记者:您是怎么保持好奇心和觉察力的,天性吗?
张亚勤:这和天性没关系,我就是从小喜欢问问题。上学的时候,学校各种讲座我都喜欢去,不仅是我自己专业的讲座,其他讲座都去听,听懂听不懂都喜欢去。另外一点是要找到非同行的人,跟他们学习。比如我喜欢红酒,喜欢音乐。那么我就要找到这方面最厉害的人,像我们现在的交叉学科最厉害的科学家,向他们请教。我觉得学点新东西很有趣。
记者:您最欣赏的人是谁?
张亚勤:我认识的很多人我都很欣赏,比如我原来的导师和老板鲍尔默,跟他讲话,有的时候具体事情他也没跟你谈,但你跟他谈过话之后就是会觉得很高兴,很乐观,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还有盖茨,特别聪明。在跟他讲话之前,你会很小心,需要好好准备。跟他讲话,你会感觉自己的IQ一定要往上走。像我过去的老板,斯坦福研究院的CEO Curt Carlson,苹果的Siri就是SRI孵化出来的。他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经常让我把一个问题两分钟讲清楚。
记者:面对未来,您的隐忧和挑战是什么?
张亚勤:大的方面,我很担忧世界和平,过去讲这个可能是在开玩笑,现在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风险;第二个,气候问题,包括整个地球的居住环境问题。我真的在想这件事,过去想得比较少,包括传染病,过去都不是事,最近几年都变成事了,这个世界会不会有战争,过去说怎么可能,现在可能性小,但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地球到30年、50年后会怎么样?疫情过去认为是局部的,这两年却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挑战。
具体的挑战,把AIR做起来是一件大事,AIR现在刚一岁,还是一个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小baby,如果说这里面的顾虑,我不希望我们AIR是一个什么都做,由小东西堆起来的研究院,我希望AIR可以尝试很多事,但能做出一两件真正改变产业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