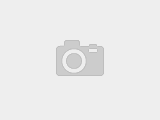近日,“元宇宙”概念大火,起因是扎克伯格把Facebook改名“Meta”(意为“元宇宙”)。

扎克伯格表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是‘元宇宙’优先,而不是Facebook优先……未来我们希望被视为一家‘元宇宙’公司。”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由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提出。在其1992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雪崩》中,他创造了合成词(meta+universe),构想了“元宇宙”的概念——只要人们戴上耳机和目镜,找到连接终端,就能够以虚拟分身的方式进入由计算机模拟、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
通俗地讲,元宇宙就是以沉浸式体验和拟真感为特征的第三代互联网,比起目前的互联网,它更能为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

一石激起千层浪,“元宇宙”的讨论迅速点燃舆论,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元宇宙架构师”的科幻作家刘慈欣也做了表态,他说:
元宇宙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内卷,而内卷的封闭系统的熵值总归是要趋于最大的。所以元宇宙最后就是引导人类走向死路一条。
刘慈欣称,扎克伯格的元宇宙不但不是未来,也不该是未来。

电影《机器人瓦力》中沉浸于虚拟世界的人类
刘慈欣曾在科幻小说《时间移民》中,畅想过人类渐渐转向无形世界的未来,在那个时代,人类虽然可以在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都有一份大脑的拷贝,但无形世界的生活如毒品一样,一旦经历过那种生活,谁也无法再回到有形世界里来。
因为对于经历过无形世界的人类来说,我们充满烦恼的现实世界如同地狱一般。

电影《机器人瓦力》中沉浸于虚拟世界的人类
某种程度上,科幻是未来的一种预演。“元宇宙”的迫近,提示了资本的侵蚀已经开疆拓土,逐渐深入到了人类的神经元和潜意识。
有人说,人类面前有两种未来,一个是走向外太空,一个是开发潜意识。
对于这样的两种未来,科幻小说家怎么看?
几年前,在《给孩子的科幻》新书发布会上,刘慈欣就这个问题有过论述,今天试做摘录,与大家分享:
问:现在年轻的、富有才华的科幻作家不断地涌现,在这些作品中,一种纯粹性、简单性、规划性的东西出现了,但是这种单纯同时好像有着某种封闭和自洽,没有您作品中互相矛盾、充满张力的某种东西。就这个问题,请您谈谈,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化当中的中国状态,跟科幻的可能性。

刘慈欣:您说了两点:一个是封闭性,一个是单纯性。这确实是对科幻文学发展现状一个很深刻的概括。我觉得它的单纯性是来源于三点:
第一,以前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枷锁与负担,年轻作家没有了。
第二点,随着我们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新一代作家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员。这两点我不想多说。
关键是第三点,科幻文学的封闭性是整个人类文明状况的一个反映。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是内向的发展,我们60年代登上了月球,到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往前走,而且连月球也没有再上去过。
而整个人类最飞快发展的技术,其实是内向的技术,就是网络技术、IT技术,它让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内向,以至于很快这一天就会到来:我们只要一辈子封闭在一个房间里面,不用出门,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度过一生,可以体验世界各个地方所有的风景。

这样就让人类的整个文化变得越来越内向,新一代通过VR体验星辰大海,没有必要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开拓——这是人类文化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反映在新一代的科幻小说中。这个变化是好、是坏,我不想评论,但是作为科幻作家,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有无数种,但是不包括星际航行的未来,不管地球上多么繁荣,那都是一个黑暗的未来。
像我这样一直描写星辰大海、描写太空的作家,不但在美国,在中国也是比较另类的作者。
现代科幻的黄金时代是美国的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那时的科幻文学,充满了一种乐观的、进取的、开放的精神,之后的科幻文学更多关注科学的负面作用,以及负面作用带来的非常阴暗的未来。(这个总结有时候不能全面概括黄金时代和后黄金时代科幻文学的不同特征。)
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也有描写未来的大灾难,像《未来基地》,有一部分是80年代写的,有一部分是更早写的,也描写遍及银河系的灾难、也有世界的毁灭,之后撰写的部分也有对未来的乐观的描写。
更切中实际的说法是,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是一种开放的、外向的文学,而之后的、我们现在的科幻文学都变得内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本质的区别。
问:你经常谈到外太空开发的主题在消失,认为外太空开发在世界范围内放缓停滞,你怎么看当今世界的科学发展,以及今天世界的选择?

刘慈欣:现在,“未来”的概念已经迫在眉睫,当代中国社会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未来感,而未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吸引力。
这样的时代症候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科幻小说比以前更受关注。戴锦华老师说美国科幻是应用文,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出现了。
提到外太空开发,与上个世纪60年代相比,它确实渐渐地边缘化了,也没有往前推进。因为整体来看,外太空开发的文化和我们现有的文化相矛盾,因为它是一种在短期之内,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一项事业,并且投入是相当巨大的。


1969年7月20日,三名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科林斯和奥尔德林驾驶的阿波罗11号飞船从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成功登月。据肯尼迪《我们选择登月》,当时的登月预算为每年五十四亿美元。
在我们的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文化下,这和主流价值体系是相矛盾的,所以人类想大规模地开发太空,首先得大规模地改变我们的文化——很可能在人类社会发生第二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开发外太空——但是现在很难。
我们现在像启动IT市场一样,用经济手段启动太空市场,也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所以我觉得,这就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表现的空间,因为科幻小说的空间是不断地被现实所蚕食的,任何科幻小说描写的东西只要变为现实就平淡无奇了。太空开发被停止了,科幻小说还保留着想象的空间。
问:作为文学体裁,科幻文学最让你珍视的一点是什么?
刘慈欣:科幻文学作为文学题材让我最珍视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文学的潜意识中,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
但是现在的科幻文学,一个很本质的变化,就是信息社会把人分成了一个一个真正的个人。在现代的科幻文学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它正在解体、消融,这个形象渐渐模糊了。
这个我认为是科幻文学相当深刻的变化。
我自己是在努力抗拒这种变化的,我自己写的作品中,人类还是作为整体出现的。我选到《给孩子的科幻》里面的小说,人类也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我接触科幻文学的时候大概还是文革时期,那个时候还没有科幻出版,也没有科学幻想的概念,我是看50年代凡尔纳的作品才接触到科幻文学,之后看到了西方翻译的科幻小说。
科幻现在变得和那个时代确实很不一样了。对这种变化,我也是有很迷茫的感觉,我也看不清科幻文学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从当初接触科幻的那种很清晰的想象、很多的激情,到现在变成了一种对科幻未来很迷茫的状态。

戴锦华:我记得80年代,我刚刚到电影学院任教的时候,读过一本类似未来学的书,它讲述资本主义的瓜分已经完成,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东西:一个是外太空,一个是潜意识。
而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清晰地开发人类潜意识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是完全毒品化的,直接作用于神经元,给你提供快感,给你提供满足,这是所谓二次元、宅文化——在这样文化环境之中的个人主义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大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共享的个人主义,多少带有英雄主义的味道,它是在社会意义上的个人;而今天的“个人主义”是在一个没有参数的意义上、绝对的个人。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其实科幻写作中始终有一个主题,就是人类究竟作为社群、还是作为种群延续下去?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延续人类的社群?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彼此相关的、有社会意义上的存在吗?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科幻的,同时是现实的和日常生活的。
所以回到《给孩子的科幻》这本书,为什么要给孩子读科幻?为什么大家都在读科幻?我们在科幻当中读什么?
我觉得没有比科幻更恰当的镜子,把我们的现实表现出来,因为现实主义如此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