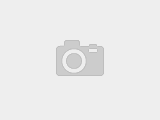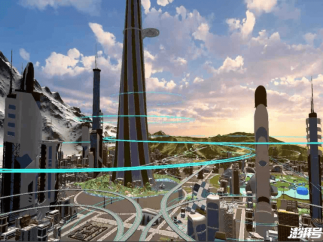李伟说:势不可挡的元宇宙时代已经到来,如果将其与传统互联网对比,那么传统互联网是现实与现实之间的连接工具,而元宇宙是连接工具尽头的另一世界。面对一个全新世界,立法滞后于现实生活的矛盾更加的突出。如何应对元宇宙带来的立法、司法挑战?现有法律规则能否适用、如何适用?是否需要建立一套全新规则以保障秩序?本文先就元宇宙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与刑民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以供参考借鉴。

一、推开元宇宙的大门
元宇宙(Metaverse)最早出现在1992年出版的小说《雪崩》中,由 Meta (意即“超越”、“元”)和 verse (意即“宇宙 universe”)两个词构成,即超越宇宙的世界。一个现实世界里的外卖员进入虚拟世界,摇身一变成了超级英雄,这个虚拟世界在书中就被称作元宇宙。而这个概念一直沉寂,到如今再次火热起来,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产生出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及VR眼镜等穿戴设备,竟真能将书中这个沉浸式、破次元、跨维度的三维共享空间再现,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随即出现。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自选身份、建立规则、创造文明、与人社交,而穿戴设备的传感技术也会让你身处虚拟却倍感真实。
二、元宇宙所涉虚拟财产相关
法律问题
元宇宙的出现,必然引发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现实与虚拟世界链接环节纷繁复杂法律问题的显现,其中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首当其冲且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在李某某诉北极冰公司娱乐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北极冰公司作为游戏运营商需要对玩家虚拟财产的丢失承担责任,判决其恢复李某某游戏账号中的装备。
那么,“虚拟财产”究竟是不是财产?如果是财产,属于何种类型的财产?如何保护?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确定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对其进行保护的基础和解决其他问题的依据,具有定纷止争的现实意义。
(一)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虚拟财产在法律上的界定并不明确,但如将它界定为“在网络空间内依靠电磁数据为载体且具有财产价值的财物”,会使得虚拟财产的范围相对确定。
《民法典》127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了虚拟财产以法律定位,即其可以作为民事财产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那么究竟作为物权、债权还是知识产权来保护呢?
首先,将虚拟财产认定为物权颇有不当。物权的支配是人对物的实际控制从而维护现实世界里物的占有秩序,而虚拟财产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用户只能通过电脑、依靠网络、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电子操作,一旦离开虚拟空间这种电磁记录便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人对其控制力较弱。而且虚拟财产由于其可复制、删除等特性或是通过编写代码,很大可能会出现凭空增加、减少或灭失的情况,导致物处于无序变动的不确定状态,这直接违背了客体的确定性要求。
其次,关于虚拟财产为知识产权一说,该观点主张虚拟财产是通过人机交互而获得的智力创造性成果,应作为知识产权来保护,但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性,这意味着其内涵和类型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自己创设新的知识产权类型,如此一来会极大地增加立法成本。
相较之下,笔者认为债权说在现有调整手段中颇具优势——主张用户与运营商之间存在无名合同关系,优点在于可以绕开虚拟财产的定性问题,转而用合同法律关系解决纠纷。之所以能做如此处理,原因在于用户对虚拟财产行使权力对于运营商具有极高程度的依赖性,即使是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也可以转为每个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两两之债逐一解决,以此作为民法领域的权利救济手段。
(二)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1.关于虚拟财产在刑法中的法益属性
把虚拟财产直接解释为刑法中的财物来保护多有不当,比如在网络游戏中,玩家A故意将玩家B养的宠物狗毒死,也不可能承担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刑事责任,即使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中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因此,简单粗暴地将虚拟财产与实际财物同等对待的处理方式显然不符合实践要求。
既然一概而论的方式不可行,就需要对虚拟财产进行剖析。虚拟财产的存在和价值以不同形式及于虚拟世界、现实世界、虚拟和现实连结的第三界——对应现实世界,虚拟财产具有相应的实际价值,必然属于刑法保护的范围;对应虚拟世界,虚拟财产以其本身形式存在,不属于刑法调整对象;对应虚拟和现实连接的第三界,主要以代码和数据形式存在,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也属于刑法的调整对象。基于笔者认为虚拟财产权利目前更适宜按照债权关系来调整,那么作为债权凭证,根据权利凭证丢失是否通常会导致财产的实质性减损以及虚拟财产的种类,可以从可挂失和不可挂失两类分别进行分析。对于不可挂失的虚拟财产(如游戏装备),用户无法通过自行操作恢复,必然导致实体权利的损失,那么只要盗得就成立盗窃罪既遂,即使未作使用;对于可挂失的虚拟财产(如账号),虚拟财产的丢失并不会必然导致实际损失,通过运营商提供的找回服务可以自行找回被盗账号,如附属于账号之上的虚拟物也被一并找回,则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只有行为人处分了该虚拟物,导致被害人在实体上遭受财产损失的时候,才能认定为盗窃罪既遂。在上述情形中,如果盗窃虚拟财产是通过对运营商的既定编码和数据进行入侵、破坏实现的,侵犯的法益又增加了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和运行安全,其行为同时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罪或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2.关于虚拟财产的量刑数额认定
针对虚拟财产犯罪量刑的数额问题,一直以来是实务界难题,比如玩家A窃取玩家B的游戏装备并降价出售,如按照平台统一定价作为量刑金额往往导致金额过高、量刑畸重,而按照过低的销赃价格量刑,则无法起到应有的刑法保护作用。鉴于此,在司法实践中倾向于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解读时指出:“鉴于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适用盗窃罪会带来一系列的实务问题,特别是盗窃数额的认定,目前缺乏能够被普遍认可的计算方式,因此对于此类案件不宜按照盗窃处理,如果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可以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计算机犯罪处理。”《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或者造成1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可以依照我国《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以及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
可见,针对虚拟财产的犯罪若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在犯罪金额认定方面存在困难,相比之下,“违法所得5000元”的认定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很多法院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罪名的规定来处理盗窃虚拟财产的案件。但是,由于计算机犯罪的量刑普遍偏低,以此类犯罪论处是否能罚当其罪,以及实践中因为罪名适用的不统一导致量刑不均衡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去解决。
例如,在“张磊盗窃案”中,张磊利用黑客程序非法侵入苏州金游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库服务器,给自己增加了游戏币“银子”40多亿两并转售牟利16余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同年发生的“陶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案中,陶锋窃取“通吃”游戏中的“扎啤”道具60亿件并借此非法牟利近19万元,却仅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2年执行。可见,金额相似的窃取虚拟财产非法牟利案件中,以计算机犯罪认定的刑期竟比盗窃罪认定的结果轻数倍之多,不仅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威慑效果相差甚远,而且定罪量刑上的不均衡不统一也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
结语:综上,笔者认为,在民法领域,虚拟财产按照债权来保护更具实操性,可以运营商为媒介层层追索;在刑法领域,可将虚拟财产拆分为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财产本身、现实世界中的实际价值、虚拟和现实连接的计算机代码数据三类,后两者属于刑法的调整对象,同时可根据窃取手段的不同,分别按照单一盗窃罪或盗窃罪与计算机类型犯罪想象竞合处理,而量刑金额应则应当尽快统一计算依据与标准,客观评价虚拟财产的现实价值,方能不枉不纵,更好地对此类犯罪进行打击和预防。
参考文献:
1、梅夏英:《虚拟财产的范畴界定和民法保护模式》《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5期
2、欧阳本祺:《论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政治与法律》2019年9期
3、田宏杰、肖鹏、周时雨:《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刑法保护》《人民检察》2015年5期
4、张弛:《窃取虚拟财产行为的法益审视》《政治与法律》2017年8月
作者简介

李伟,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事务部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斗政策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在某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十二年,独自或参与办理国内影响重大的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数百起,并参与了量刑指导意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涉税犯罪、毒品犯罪等司法解释、审判参考文件的起草、编写工作。曾荣获某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及“嘉奖”多次。
赵蕊,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李伟主任助理,硕士毕业作为北京市海淀区党外优秀大学生培养人才,曾任区属某国有二级企业经理、法人,以及区重点创意产业园区的运营及创新业务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