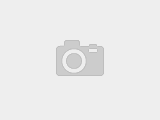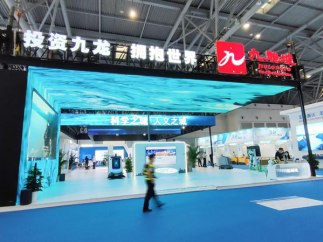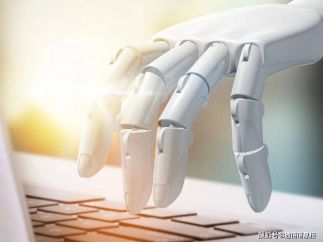在《三体》诞生前,《超新星纪元》曾被认为是刘慈欣的最佳长篇小说。该作初稿于1989年,期间五易其稿,经手编辑近20位,历时14年才得以在2003年于作家出版社出版。颇为遗憾的是,在众多关于刘慈欣科幻作品的研究中,《超新星纪元》这样一部倾注作者大量时间、精力与心血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原因或许在于这部小说世界设定的主体是孩子,批评者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儿童文学。尽管在内容及科幻元素的核心创意上,《超新星纪元》尚不能与《三体》系列小说境界的空灵之美及其以宇宙为背景的宏大与深邃之感相媲美,但它也绝非是简单的童话小说。
同短篇小说《流浪地球》一样,《超新星纪元》所采用的科幻创意是刘慈欣较为青睐的恒星“氦闪”爆发现象,但在故事情节的演绎上两者截然不同。前者面临即将到来的太阳“氦闪”危机时,具有浓厚家园情怀的中国人选择带着地球流浪太空,谱写悲壮的太空歌剧;后者设想御夫座的一颗恒星“氦闪”,强劲的粒子洪流产生的射线破坏了13岁以上人的基因,地球成为了一个只剰孩子的世界,人类社会面临重构。相对于刘慈欣其他科幻小说对科学技术的关注,《超新星纪元》将精力更多地放置在社会运行规则的改变上,一个只剩孩子,家庭结构就此消失,秩序被打破,伦理与道德规范渐趋失效,单纯依靠人类儿童时期的本能和欲望推动的社会应如何维系?孩子世界真的会如诗人纳奇姆·希克梅特诗中所希冀的“把地球交给孩子吧/哪怕仅只一天/让世界学会友爱/孩子们将从我们手中接过地球,从此种上永生的树”那般纯洁无瑕吗?
有意味的是,刘慈欣将问题放置在隐于现实背后的赛博空间进行探讨。当互联网尚未在中国全面普及之时,计算机工程师出身的刘慈欣就以其前瞻性视野在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中以赛博空间为载体,通过孩童对“好玩”世界的幻想,肆意架构他的元宇宙,这与《雪崩》中戴上与终端接驳的头盔就能进入虚拟世界的构想不谋而合。类似的设定在稍后的《神经漫游者》《异次元骇客》《黑客帝国》《头号玩家》等科幻作品中屡见不鲜。诚如人大教授刘永谋所言,元宇宙概念属于“新瓶装旧酒”,它不过是赛博空间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赛博空间的“高级”阶段。赛博空间同信息社会一样,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是人们试图了解现实世界重要特征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小说是呈现这一形式的最佳文体。因此面对“元宇宙”的再度兴盛,对《超新星纪元》进行重新释读有其现实意义。
小说中,超新星纪元之初,面对大人的离去,精神失根、无所依靠的孩子们被无边无际的孤独和恐惧压倒,这种心理失衡的大众效应使国家在运行之初陷入混乱。帮助孩子们渡过危机的是大人们留下“中华大量子”超级计算机,它以数字国土为依托,模仿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并行结构,使得管理国家成为可能。进入“惯性时代”,孩子们在学习之余承担起大人的工作,累、无聊以及失望的心态充斥着整个社会,而依靠“大量子”和网络建立起来的虚拟空间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刺激,诱发了更强的情感投入,最终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了无生趣的现实世界。
尽管“元宇宙”在现实社会中尚未成形,许多问题也有待明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元宇宙”并非因自身而火,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倦怠期。身处加速前进,越来越“内卷”的机器社会,人们被时代的洪流席卷,诸如“佛系”“躺平”“摆烂”的心态开始弥漫,而此时媒介技术的成熟,使得“元宇宙”有了从幻想变为现实的可能,其出现恰好可以提供一个出口,弥补人类在荒漠世界精神层面的缺失。“元宇宙”和人类天性中“玩”的特点有着天然的联姻关系,游戏的规则早已深深嵌入人类文明的基因,在虚拟世界,人类追求享乐和游戏的本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和释放。就某种意义而言,游戏和人类文明的起源与童年时期息息相关,而“玩”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玩”重建社会秩序?未来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游戏机制,为教育、文化、社会制度提供游戏式的奖惩机制,激发更多人的积极性?或许正是30多年前刘慈欣《超新星纪元》思索的问题。在孩子世界,驱动成人社会运行的货币齿轮早已不奏效,“好玩”才是推动孩子世界的真正动力与最大意义。孩子们在“新世界”召开全国大会,同小领导人对话,纷纷要求建设一个好玩的世界以摆脱沉重的现实,他们凭借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建设了一个虚拟国家,在这里所有的孩子住在一栋搭载火箭电梯的300万层高的大楼里,剩余的国土面积被规划为游乐园区、天然野生动物园区、探险区以及糖城开发区等,以凝聚起整个儿童社会。
为了实现幻想中的乌托邦,孩子们在虚拟社区召开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讨论,他们汇聚在虚拟“广场”上,参与人数多达两亿,孩子世界狂热的面目也终于在这个虚拟空间呈现出来。经过大量的数据处理,孩子们的发言被归为两派,其中支持在现实世界建造虚拟国家的“虚拟公民1”占比达91.417%,而极少数的理智群体“虚拟公民2”只有8.972%,孩子政府一时陷入了困境。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人类的群体效应十分强大,这在一场有几万观众参加的足球赛中就能表现得很明显,而当两亿孩子站在同一个广场上时,这种效应之强大,是以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想都不敢想的。在这里,个体在精神上已不存在,只能融入到群体的洪流中……他们当时已完全失去控制,什么理智什么逻辑,对这亿万个娃娃已彻底失去了意义”。其实,类似的群体形象书写始终贯穿着刘慈欣的创作,如《三体》中狂热年代的群众、《乡村教师》中愚昧麻木的村民、《流浪地球》中自以为是的叛军、《地球大炮》里目光短浅的百姓、《全频带阻塞干扰》里愤怒失智的人民……这些不同样貌的形象,在《超新星纪元》中便是遵循本能欲望,肆无忌惮的孩子们,这几乎可以看成是刘慈欣人物塑造的原点。刘慈欣将孩子作为成人世界的映像,重思社会化过程的合法性,并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建构及价值取向作了深入的探讨:如何保证社会运行基本的物质需求?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应如何平衡?绝对的民主是否会带来民主泡沫?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想象和推测,为读者建构一个可能性世界。
眼下信息时代的发展速度早已超乎世人预料,各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脑机接口等领域大规模投入资金,人类文明正以不可抵挡之势走向赛博文明,“元宇宙”也走向了更高级的全身沉浸式的赛博空间。2018年,刘慈欣在获得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时再次表达了他对元宇宙的批判态度——“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言语间透露着一个科幻作家对赛博文明的深重忧虑与不安。
相较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和王晋康《蚁生》使用化学手段使人获得幸福的乌托邦,《超新星纪元》中通过技术手段让人甘愿从全景敞视监狱走向电子牢狱,沉浸虚拟空间自我麻木获得满足的赛博乌托邦显然更加凶险,这些技术更加让人迷惑于存在的意义:在真实的“痛苦”和虚幻的“快乐”之间,生命将何去何从?至此,刘慈欣停笔不再想象人类在赛博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中的生活,将反思的空间留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