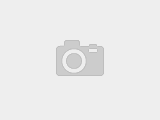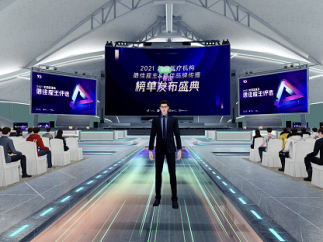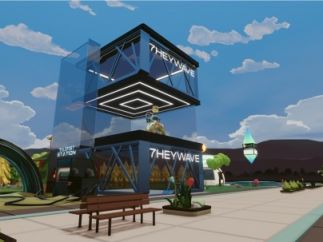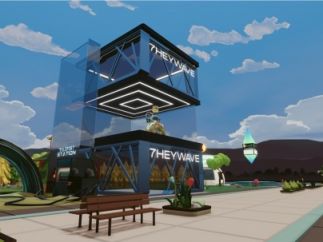“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这样的场景正在博物馆中成为现实。过去一年,敦煌推出的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吸引了万千目光,故宫在深圳的沉浸式数字体验展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数字技术和文博行业的结合远不止于此。
8月4日,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数字技术展大美中国”主题论坛上,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于俞天秀、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副主任于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交互媒体艺术设计研究所所长张烈、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数字中轴”项目负责人李汶轩以及易拍全球研究院执行院长祁煜琨共话数字技术如何激发文博艺术新动能。
敦煌研究院和故宫的数字化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其中,敦煌尝试用数字技术保存莫高窟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则启动了“数字故宫”的建设。
此次,俞天秀和于壮的对话颇受业界关注。俞天秀是典型的技术出身,而于壮则是艺术出身,这场对话也被形容为“技术和艺术”的碰撞。在俞天秀看来,文博数字化应先从广度上了解文化遗产,再从深度上挖掘文化遗产的价值,之后再用科技技术助推文化遗产,这样才能取得更大效果。于壮表达了他对故宫未来的浪漫设想,希望尝试用数字孪生技术复现一个真正的数字博物馆,能够将线下真实物理世界的博物馆实时、动态映射到线上虚拟世界,甚至可以对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开展预测性保护、研究、管理等工作。
谈及数字技术和文博艺术交流互鉴时的痛点,于壮称,很多科技企业的数字产品或者技术本身很好,但是放到故宫谈融合再创造时,就发现不行,这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博物馆没有足够的、深厚的认知。在他看来,所有科技企业一定要尊重历史、敬畏文化。
俞天秀结合敦煌的地理位置说,敦煌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生活也不太方便,很多人来了以后可能因此退缩。另外,莫高窟有492个洞窟,每个洞窟形制都不一样,每个洞窟的技术应用可能都需要定制化研究。不少有成熟产品的单位不愿意为敦煌研究院一家改变自己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化
文物转化成数字资源,实现永续传承、沉浸式体验
新京报贝壳财经:从展览展示、保存保护以及创新发展等方面看,数字技术如何给文博艺术进行赋能?
俞天秀:敦煌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尝试用数字技术来保存莫高窟的世界文化遗产,初衷是用数字技术记录文化遗产的信息,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的。一方面,永久保存是用数字化技术记录文化遗产的信息,永久地保存在计算机里。另一方面,数据保存后,就是永续利用。现在我们也在保护、考古、美术临摹、展览展示、敦煌学的研究及其他很多方面用上了数字化数据,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确确实实地永续利用阶段。
于壮:俞天秀所长从甘肃远道而来,让我想起了去年在故宫举办,并引起社会热烈反响的故宫敦煌特展——主题就叫“敦行故远”。今天看到天秀所长,顿时有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亲切感。
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都是国内文博行业在数字化方面探索的“排头兵”,我在故宫从事数字化建设工作接近20年。故宫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博物馆:世界级遗产地、国家一级博物馆、5A级旅游景区,在这样的格局定位下,又伴随而来三重属性,这些年故宫的数字化建设过程就是围绕着这三种属性开展应用和探索的。
一是文化遗产地的唯一性,故宫、敦煌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基于这样的唯一性,故宫所有数字化工作最核心的要义就是文化遗产保护。跟敦煌一样,20世纪90年代故宫也启动了“数字故宫”的建设,建设之初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少进文物库 多进数据库”,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尽快地把故宫大量的、丰富的、不可再生的实体文物转化成数字资源,做到永续传承,同时也支持博物馆的各方面工作。近些年,故宫博物院通过互联网平台,成为国内首家把馆藏186万余件文物名录全部进行公开的博物馆,同时我们也启动了故宫数字文物库整体建设工作,有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二是基于博物馆的多元属性。故宫不只是一个文化博物馆,还是一个宫廷博物馆、建筑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为富含多元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这就需要不停地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用数字的方式和手段把它再呈现出来。比如在深圳的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以及“畅游多宝阁”小程序。
三是面向广大观众多样化文旅消费需求的服务融合性。基于文旅融合大背景,如何让更多观众能走进博物馆,主要还是靠文化IP(知识产权)的打造以及行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布局数字文化的服务于传播。比如这几年,故宫博物院不断梳理各类数字产品和数字内容,做统一整合,以“云游故宫”为主题聚合这些产品和服务,给观众以统一的入口,为观众提供“一站式”文化服务与体验。
张烈: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以及促进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和创新等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我重点从三个方面讲一下看法。
一是有效地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数字技术可以生成文化遗产的高精度、高保真的数字镜像,从而通过数字手段进行有效的记录和保存。这也可以说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让文化遗产以数字化的形态永续地存在,同时也是后续一系列数字服务和应用的工作基础。
二是有效地促进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其实在社科研究领域,随着数字化研究手段介入,就兴起了“数字人文”的新型研究方法。将大量文化遗产信息和知识进行数字化,就可以利用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手段建立更广泛的知识关联,便于研究者从海量的文化遗产数据中发现新的规律,生成新的故事,这些都可以大大丰富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促进文化遗产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和创新。
三是促进面向公众、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的文化传播和体验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介入,能够非常好地激发文化遗产的创新活力。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进行展示和传播,带来更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科技手段,创新消费场景,激发经济活力。从而可以让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消费三者更好地互相促进、互相助力。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看,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起步难
建文化遗产数据库存痛点,“文物数字化并非只有炫酷特效”
新京报贝壳财经:俞天秀所长曾在采访中说“文物数字化‘从零到一’的阶段是非常困难的”,李汶轩和祁煜琨两位负责人也曾深度参与到“数字中轴”项目和布达拉宫文创项目中。这个“非常困难”到底难在哪?
李汶轩:我以“数字中轴”项目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中轴线”的特殊性比较强,首先它是遗产点集群申遗项目,“中轴线”包括遗产区和缓冲区,其中遗产区有19个申遗点。“中轴线”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少进文物库,多进数据库”,但在过程中会发现这19个申遗点所建立的数字资产库并不均衡,有的已经非常完善,有的基本没做,资产的归属也在不同单位。其间,我们做了大量沟通、收集和梳理工作。总之,建立文化遗产的数据库仍有非常多的痛点,这也是接下来需要社会力量和企业共同攻克的。
第二个问题是“数字中轴”和故宫、敦煌不一样——大众对“中轴线”的认知并不强,我们前期快速上线了“云上中轴”小程序,是为了从基础层先解决大众对“中轴线”的认知问题及对遗产价值的认识问题。所以,通过“云上中轴”小程序,我们希望以创意内容和沉浸互动的方式,拉近遗产和大众的距离。同时,我们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首个数字形象IP——北京雨燕。这个数字形象选取了19个遗产点元素,结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风筝造型,以艺术语言重新创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和尝试,让中轴线的历史文化更好地触达社会大众,传播到世界各地。
祁煜琨:布达拉宫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代表了我们国家多民族手足相亲、血脉相依、和衷共济的文化典范。这就要求布达拉宫文物数字化要更加严谨。
我们认为,文物数字化,并非只有3D建模或炫酷特效,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承、传播、交流。保护是我们天然的使命,但是传承、传播、交流才是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在数字时代,包括现在我们畅想的元宇宙时代,全世界的文物所印证和代表的各个文明,如何在数字世界中沟通交流?就像咱们现在用汉语交流,全世界共用互联网协议、4G、5G通信标准一样,文物的数字世界也需要有统一维度、统一规范,来让各个不同文明的文物可以在数字链接中,以同一个基准实现对比、沟通和对话。
因此,文物数字化“从零到一”的第一步,就不能只考虑自身所参与的眼前项目,而要站在全球文明的角度建立统一的对话标准。
从去年年初到今年年初,我们研究院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组织当中,为中国赢得了全球各个文明文物艺术品数字化的“元数据标准”。我们现在可以自豪地讲,全世界文明的文物数字化,最底层的数据规范,是由中国人来制定的。
不单如此,在文物元数据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还拿到了另外3项世界文物数字化的标准制定:“文物艺术品鉴别系统”“文物艺术品数字化应用系统”“文物艺术品知识图谱系统”三个互链应用技术方向的国际标准。基本上覆盖了全球文物艺术品从“数据定义”“身份鉴别”到文物的“数字化呈现”以及延伸的“文物知识图谱”,形成由中国制定的一整套文物相关国际关键标准的链条。
我们研究院也希望将制定国际标准的课题开放,共同帮助全世界的文明,在全球数字互通的时代,学会“如何认知文物”。
关键词·破篱墙
很多技术成博物馆“过客”,科技企业要敬畏文化
新京报贝壳财经:李汶轩和祁煜琨两位负责人在做文博数字化项目时,都曾多次到一线采风,增强数字技术和文博艺术行业间的了解非常重要,那么两者交流互鉴时有没有什么痛点?
俞天秀:我们做了差不多快30年的数字化,痛点挺多的。每年,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业界觉得技术特别厉害的人或者单位,找我们说自己的技术多么先进。敦煌研究院是非常开放的单位,有助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弘扬的任何方法都可以尝试。不过,很多单位刚来时雄心勃勃,过了两三个月后就悄无声息了。也有很多单位真正是为文化遗产单位做事,踏踏实实改进自己的技术,慢慢沉淀下来,最终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敦煌可能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生活也不太方便。很多外地人可能因此退缩。另外莫高窟有492个洞窟,每个洞窟形制都不一样,真的把技术用在里面时,就会发现每个洞窟都需要进行定制化的研究,很多产品成熟的单位不愿意为我们一家改变自己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只是数字化的事,并没觉得莫高窟的价值有多高。所以很多人像过客一样,做过就结束了。在敦煌,如果合作三年时间,没有足够的打磨,基本就没有大成就或者大的成果。我们经常想到底困难是什么?一个是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问题,再一个就是本身愿意不愿意为文化遗产付出,为文化遗产定制很多内容。
于壮:我之前开玩笑说,文化和科技相遇就像谈恋爱,看对眼儿,情投意合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如果只是貌合神离,可能就不成了。事实上,技术和文化、艺术之间真有一道硬墙隔开,需要被打破?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
很多科技企业做的产品或者技术本身很好,但放到故宫,谈融合再创造的时候,就发现不行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博物馆有足够深厚的认知,这个认知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科技企业一定要尊重历史,要敬畏文化。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足够的敬畏,我觉得很难做到“文化+科技”的自然融合。
反过来讲也是一个善用技术的过程,科技跟博物馆的结合,未必就是把最先进的技术拿到博物馆用,每个数字化都要跟文化内容、文化价值的阐释有深度地自然融合、转化,所以要做到善用、适用技术。
张烈:怎么把艺术、科技、文化进行融合,可能要分几个层面来说。
艺术和科技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再加上文化,这涉及跨学科合作,以及相应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这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和保障。
去年教育部专门增设了交叉学科这一新门类,可以看出目前社会对解决综合性复杂问题的迫切需求和国家对这类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我建议要设立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方向的交叉学科,以满足该领域的迫切需求。
设立相应学科后,学科建设怎么做?这需要开展大量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需要进行相应的师资力量的培养、实验室的建设等一系列工作。
此外,人才怎么培养?我们现在缺少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方面的“导演”。这个“导演”要既懂技术,又懂艺术和文化,能够把这三个方面很好地黏合在一起,从而大幅度提升文化遗产数字创意的阐释能力、创新能力和艺术呈现效果。
当然,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所以现阶段如何做?刚才俞所长介绍了敦煌研究院所采取的开放合作做法,这很关键。围绕着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重点研究对象,各个领域的人都可以来,共同对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和攻关,在研究实践中推进学科交叉和融合创新,并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经验,培养人才,开展学科建设。
关键词·新技术
现在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最好年代
新京报贝壳财经:随着5G网络发展,移动终端不断普及,而大家熟悉的元宇宙、web3.0、AI等技术也都方兴未艾,这些技术哪些可能会用在文博艺术上?未来又会有哪些化学反应?
李汶轩:从行业大层面来说,整个行业越来越接受数字化的方式,开始打开、包容和拥抱。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数字化的力量可以让文化遗产复现,以及在数字化世界里继续发挥它的生命力。我们看到全真互联网浪潮来袭时,有太多行业内的机构、博物馆都在拥抱,腾讯也是希望把“科技+文化”的力量形成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应用到实际场景中。
在这个层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从“云游敦煌”“数字故宫”到今年6月“数字长城”上线,其中,“云游长城”小程序实现了全球首次最大规模文化遗产毫米级高精度、沉浸交互式的数字还原,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能力复制到“数字中轴”上。当然,它不仅仅只是复原和呈现,而是希望在数字场景里能更多地沉浸互动,让大家更好地感知文化遗产的魅力,这是我们接下来努力和探索的方向。
祁煜琨:刚才讲到5G、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新数字技术在最近两年突飞猛进的发展,我想现在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最好年代。
刚刚俞所长、于主任都提到,做了30多年数字化,在文物与技术两个不同专业领域的理解和沟通方面遇到各种痛点,共同期待着各方能够善用、适用技术,做到基于文化价值阐释的深度融合与转化。
对我们而言也是深感于此,我们站在数字科技蓬勃发展的当下,推行着最前沿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落地,作为执行项目的团队,我们不能按照各自想法自由或者市场化地发挥。
期望我们共同把握国家在文化数字化战略上的部署,共同规范文物阐释必然遵循文物考证的数字化学术规则,以中国考古学和探源工程的文化阐释方法,在讲述文明故事的产业应用当中,聚合各方能量,建法度、定规则,以可控规范的数字标准,为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传播、阐释,带来真正的中华文明元宇宙。
关键词·畅想
期待科技+文化在山顶握手
新京报贝壳财经:各位对于数字技术赋能文博艺术有何畅想?
俞天秀:我是技术出身,我觉得把文化遗产数字化做好或者传播好,应该先从广度上了解文化遗产,再从深度上挖掘文化遗产的价值,之后再用科技技术助推文化遗产,这样起到的效果,绝对远远大于直接用技术去做一个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工作。
于壮:我是艺术出身,对故宫数字文化的发展有很多浪漫的想法,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及数字艺术的创新发展,很多慢慢都会付之实现,未来我们可以畅想。故宫博物院现在正在探索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打造一个真正的数字博物馆,这个数字博物馆将打破看似动态的展现形式来表达静态内容的一般做法,尝试将线下真实物理世界的博物馆实时、动态映射到线上虚拟世界,甚至可以对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开展预测性保护、研究、管理等工作。
张烈: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要练内功,二是要发挥创意。练内功练的是数据,数据是基础,这很重要。创意则是要整合资源,驱动新型消费和体验场景创新。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智慧数据驱动,体验场景创新”。
李汶轩:作家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如何让科技促进文化繁荣,如何打造和积累科技文化成果,让这些成果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会是我们接下来的探索方向。期待科技+文化在山顶的握手。
祁煜琨:数字技术是文博事业未来发展和践行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手段,期望与各位前辈老师共建规则、守正发展,为文博事业贡献我们研究院的一份力量。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孙文轩 白金蕾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