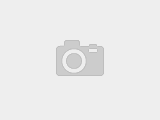劉 征
假如我今天嘗試快速的用一篇小文章來聊德里達,實在是他很需要被知道。在以往,只有文藝理論或者一些學術範圍之外的、趕時髦的人給他冠以「解構主義之父」的頭銜。然而,當我們開始談論元宇宙的時候,德里達,甚或是笛卡兒才真的時髦起來了。原因是他們在很早之前就在研究類似問題,並把這種狀態稱之為思維本身。說是思維,還太簡單,應當稱之為思維生態。它飄搖不定,令一切的意義生產都難以被完全捕捉。在局部,思維還可解,可一進入宏觀視角就不一樣了。樣樣都充滿矛盾。
不過,執拗的德里達不這樣認為。他說,一切固然是一切本身,但倘若人一旦感知到它,它就會立刻被俘虜。沒有未經感知就進入我的生活的世界,也就沒有一個無我的存在。這脫胎於笛卡兒我思我在的思想雛形被德里達用兩個概念的顛倒表示出來,以反對上世紀六十年代風靡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在結構主義那裏,是先承認了物之本體,並將它叫做能指。之後,才有人選中此物,抽出其中一個意義來,讓它為其所用。這個為其所用被叫做所指,它處於從屬地位。德里達偏不,他說:「所指在前。」顯現即對我可見,可見就是我的看見。
前一秒,每一個經歷過唯物主義訓練的人,每一個在這物質世界存身,並時刻因無法逾越的境遇倍感痛苦的人都會接受能指在前的事實。可看到德里達的論述,人人又都動搖了。因為否定了德里達,就否定了自己的感知。而我們的生存,本身就是依賴感知在生存,即便是痛苦,也是一種感覺。沒有了感知的人是不可想像的,他既然已經形同機器,那被無情的毀滅,或者被放棄掉又有什麼可惜的呢?所以,任何關於人工智能無限強大的技術決定論傾向一定會招致激烈的對抗,因為人工智能作為人的創造物,唯一創造不出來的就是內在只能為個體所感知到的情感。即便一個機器人,被創造出了眼淚,即便一個互聯網絡,當時有高興、悲傷、氣憤,但那都是給別人看的。真正的情感,是一種自我感知。表達是次要的,感知才是主要的。
德里達以關注人的方式關注感知,他令一個外在結構靠邊站了。或者,使其成了一個工具的外在,激發着自我作為認知和情感的自我。一個出生在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居民,一個在阿爾及利亞大鬧着要脫離法國的時代,有一個叫做德里達的人自始至終都在自我承認的路上走着,讓我們熱烈歡迎他。
德里達給我們在發現自我和認識自我、並最終承認自我存在的路上建立起來一個榜樣。並且,他還讓這個自我成了一門科學。變成了《論文字學》、《聲音與現象》、《胡塞爾現象學中的起源問題》等等。一個比元宇宙還早的元宇宙理論,比朱克伯格這些技術派狂熱的創造元宇宙更理性的人本主義。他並不想要製造一個所有人都在其中的異想的抽象世界,這個世界或多或少有些避世的味道。就像一種精神,愈複雜愈完整倒不見得真的值得慶祝,因為思維的縝密都是在遇到麻煩的時候才被迫添加細節。德里達願意將一種純精神回歸個體的內心,而且堅守了一種內在性情原則。這不是侵略,僅是在為個人辯護而已。而這才是好的元宇宙,在給心靈帶來慰藉的同時,又與身體和生活不相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