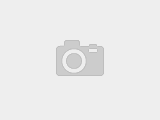元宇宙创造了一种技术主导的时空模式,因而引发了广泛关注,或不容否认,已为期三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元宇宙的快速发展。后疫情时代,或许我们将诸多美好的想象都寄托在技术革新之中,但往往忽略了疫情带来的社会转型变化本身或许远远比技术要深刻、复杂。
元宇宙可能在很大概率上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实现,而在今天,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元宇宙可能已成为一种社会概念。在我们今天畅想元宇宙未来愿景,担忧元宇宙新生的伦理/道德风险之时,我们更应该担心后疫情时代“元社会”的到来。

元宇宙社会的时空性:时空折叠
时空折叠是一种因为强大的引力使空间发生扭曲的现象。或许疫情便是这一强大的引力,加速着我们的时空折叠。如同诸多以时空折叠为隐喻的文艺作品所揭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都仰赖于时空性,这种时空性是物理和社会意义的交叠。以空间区隔映射阶层断裂的世界观设定,固然是社会阶层差距的具象化寓言,但后疫情时代,社会时空的边界或许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
“时空”是贯穿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理论核心主线。吉登斯强调,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的基本属性,一切社会互动都是嵌置(situated)在时空之中的。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时空界限的弥合,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正在将我们的社会分离成多个并行的时间化空间。在变化的社会秩序中,社会群体内部的差异并不罕见。但问题在于,在数字社会时代和疫情的交叠影响,空间隔离带来了时间维度上的并行,同样的时间条件下,由于疫情不同地方/空间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却又通过网络高度关联在一起,因此不同的社会群体内部逐渐分裂形成诸多“茧房”,向内吸收同质信息,向外散播同质观念并挤压异质观念的空间,最终形成观念的极化和对峙的激化,从而构成一种“时空折叠”。“时空折叠”使得现代化“后发”社会的人群同时面对着历史悠久的原生系统记忆和新生的外来系统记忆,催生了社会不同群体内的观念分化,最终导致不同群体共同占据集体记忆,但在时间里此消彼长、分享空间的记忆割裂。
和前疫情时代数字互联带来的时空折叠不同,疫情的到来作为突发事件要素,将时空折叠进一步从虚拟空间扩张到物理空间,物理空间得以时间化,在同样的空间类型下, 或许因为疫情或其他社会属性的不同,导致产生的社会事实、社会互动完全不同,且这种互动形态和事实构建具有极强的约束性和普遍性。与此同时,时间也因此空间化,在相同的时间维度,不同的社会情景事实完全不同,且以群体形态存在,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里,因所处空间的不同,导致了所产生的社会行为存在明显的隔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时空折叠真实地在事实生活中产生极大的影响,社会时空在行为事实基础上逐渐交叠。
元宇宙社会的连接性:部落主义
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是部落动物。我们需要从属于群体,这也是我们总喜欢加入俱乐部和组队的原因。一旦人们与群体相联系,其身份会与该群体绑在一起。他们会按自己的群体身份认知为所在群体实现目标或谋求利益,对抗和惩罚外人,极端情况下甚至造成伤亡和杀戮。
社会学家马费索利预测,当文化和现代主义的机构衰退,社会将接纳怀旧之情,并在过往中寻找组织原则。因此,后现代时期正是新部落主义的时期。新部落主义,或称现代部落主义,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假定:当代人类已发展成部落式的社会、而非大规模式的社会,也因此人类的社会网络将形成独特的“部落”。
更适当的隐喻可能是“分裂”事件,如在历史上宗教派别的分裂,例如逊尼派从什叶派脱离,或是新教从天主教分离。当今的“部落主义”似乎与“宗派主义”有本质相通之处,尤其当我们试图理解近年来兴起的极端主义,重点不再在于“部落”间宗教、科学等依据差异,而是“政治认同”。对方不仅仅是错的,而且是邪恶的。我们这一方不够纯洁的人都是“叛教者”。宗派主义一般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非我族类”,亦即将对手视为本质上与自己不同或异类的倾向。第二个要素是“厌恶”,亦即对对方怀有强烈憎恶感和不信任感。第三个要素是“道德化”,亦即认为对手奸佞邪恶甚至是犯罪分子。
过去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网上不时充斥各类无法证实的消息,左右着人们的看法。紧张复杂的国际局势,也导致不同立场之间的争论尖锐化。这种尖锐和极化超越了我们过往对分歧的包容性,逐渐演化成一种执着于某种观念的坚持或对另一种观念的对抗,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只信任或只认同自己这一方,而在人们轻视另一方,认为对方“非我族类”并且更加不道德,这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存在威胁。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这种宗派主义或者部落主义的基础可能已经远不是宗教或部落认同本身,而可能是一种“知识理念”、一种“科学观点”、一种“叙事话语”,已经超出了可以经过严谨科学精神所证伪或证实的范围,也超越了自启蒙时代以来逐步建立地理性沟通的议事范式,而更多是一种被动的立场选择,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次没有退出机制的竞争,过去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成机制逐渐崩解,群体只会按照立场采取行动,逐渐进入一种元社会阶段。
元宇宙社会的独立性:个殊性的兴起
社会结构的转变促使文化面貌也面临剧变,每个个体都面对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的危机。德国社会学家Andreas Reckwitz的新书《个殊性社会》(Society of Singularities)以近年来孤狼式恐怖袭击比例的剧烈增加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现代社会结构下每个个体的处境。Reckwitz以文化社会学角度窥探主宰后现代(后物质主义)社会的个殊性(Singularity),并首先由社会逻辑切入,指出文化资本主义、数字化技术的崛起以及新中产阶级截然不同的美学观点,衍生出有异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个殊性。个人主义依然强调彼此之间享有同等的权利和采用同一行事规范,而个殊性则另指个体与众不同的原创性(Originality),并以之为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本,不同个体之间存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个殊性社会》(Society of Singularities)书封
与“晚期现代性”及其普遍存在的社会“个殊逻辑”相反,现代性的前几个时代以“普遍逻辑”为特征。普遍逻辑需要社会实践和制度在技术、认知和规范上的合理化,它强调和复制标准化、形式化和普遍化的观察、评估和生产,以及挪用客体、主体、空间、时间和集体的方式。“资产阶级现代性”(约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和“工业现代性”(约 1920 至 1970 年)从根本上遵循了“普遍的社会逻辑,即推动标准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然而,自1980 年代以来,个殊逻辑越来越多地开始塑造经济、工作、生活方式和政治倾向,因此我们“在现代性晚期正在见证社会的结构转型,包括一般的逻辑让位于个殊的逻辑”。
而个殊性介入政治场域的直接后果便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集体行为运动模式。单一的逻辑体现在政治格局中,首先是通过一种“专有的和差异化的自由主义”,在这种自由主义中,民主制度里的传统政治精英就显得进退维谷,以为中间落墨就皆大欢喜,实际却两面不是人,谁都不高兴。
疫情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剧了个殊性的存在。疫情时代因为时空的隔离,无异于使个体成为一种竞争性的注意力资源,尤其是个体间的不可通约性随着物理交流的缺失和数字时代“附近”的消失而变得格外突出。但是看似疏离的个体又在部落主义中以一种极端和机械的方式整合或被整合到一起,从而构成了一种机械的连接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同在互联网平台上,看似相连的一个个个体,却在激烈的观点对抗与冲突中,加强着不同通约性,彼此不再可以被理解、被接受。
后疫情时代,或许我们已经走入了一场元宇宙社会的加速路径,这已远超技术进步带来的体验革新。更重要的是,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匹配滞后,或许将我们的真实生活进一步部落化、个殊化,以至于失去了真实社会互动所带来的有机整合可能。这种社会有机属性的丧失将会带来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和极化,需要我们有超凡的想象力弥合独立而机械连接的多重宇宙,而一旦我们错过了时空弥合的整体性、连贯性、有机性窗口,社会元宇宙化将伴随更大的风险涌现。因此,我们需要用审慎的、共情的、动态的和系统的眼光和行动去连接部落之间、个体之间以及部落与个体之间出现的鸿沟。相较于技术,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一种新形态元宇宙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