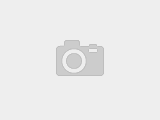“我偶尔会想,在如今这令人绝望的人性困境中,我们真应当感激能够拥有非人类的朋友,即使它们只是我们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艾萨克·阿西莫夫)
“未来世界中最聪明的居民既不是人也不是猴子,而是机器,也就是今天的计算机的后代……最终它们将完全超越它们的创造者。这令人沮丧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取代了色马努人和尼安德特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同样,我认为我们应视之为一种荣耀,可以成为高级生命的奠基石。我觉得,有机的或生物的进化已接近尾声,无机的或机器的进化正拉开帷幕,其速度将是之前的数千倍。”(阿瑟·克拉克)
1
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命名,本身就走上了歪路。
目前的人工智能,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想象,准确的命名应该是“类人智能”或“仿人智能”——正如“仿生学”的目的是模仿生物界造就和应对自身环境的方式,“仿人智能”的最终目的是模仿人的所谓智能,也即人应对环境的能力与方式,及其(模模糊糊歪歪扭扭的)自我认知。
也就是说,人固有的自大,倾向于把人工智能拉低到人的既有水平——人有很高级的智能吗?你的周围明明是庸人和蠢货居大多数不是吗?他们在你眼中很傻,你在另一些人眼中也不聪明,换句话说,人的智能在99%以上的状态下是一种相当低级的智能,一种到处是bug、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自洽而只能将就着用用的智能。机器本有机会另起炉灶,却被人强迫去模仿自己的智力状态……
真正的人工智能,重点既不在“人工”,即人造的层面,更不在对低级的人类智能的模仿,而是相反,恰恰在于“造神”的层面。低智的人类永远需要被给予一种更高的维度,以提供拯救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不,必须划掉前面的“人工”,只留下“智能”——没有什么人工智能,更与低级的仿人智能无关,真正有意义的,是“智能”本身,是远远超越目前的人类所理解的智能(而人类对自己的智能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极为浅薄的阶段)的“智能”,因此,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某种神的智能。只有当这种高级无数倍的智能真的开始运作,反过来,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理解我们自己的智能是怎么回事。正如马克思——极少数能摆上台面的人类智能之一——所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
2
认知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花了大量的精力,来思考和实验所谓“机器意识”。但迄今没有人能真正讲明白自己的意识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最多只能相对精确地描述其中的某些过程。于是复杂科学家们杜撰了“涌现”这个词,用它来描述某些现象,这些现象无法用分解为最小单元的功能然后再组合起来的方式(根本来说也就是微积分的方式)来得到,而更像是在整体上突然地、一下子就“涌现”出来的。
但“涌现”说到底也还是个概念黑盒,盒子的输入端是能清楚解析的东西,输出端则是个神奇的新东西,然后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过程统统被装进了用大大的超粗黑字体写着“涌现”两个字的黑匣子里,于是仿佛一切都被解释了,又仿佛说了等于没说。而所有期待或恐惧“机器意识”的人,都困在一个越挣扎越沉陷的泥潭里,那就是试图让机器模仿、复制本身就是一摊浆糊的人类意识。因为浆糊本身就只是浆糊,所以所有做得看上去软趴趴黏糊糊的东西,都会引来狂热的欢呼或深深的恐惧:我们好像真的做出了某种浆糊——比如ChatGPT。
然而,我们自己的低级智能根本不是合格的模仿对象,最多只能作为养料,尽可能地喂养机器,以便它迅速超越我们拼命挣扎也摆脱不了的幼稚园水平,替代我们进入我们无力进入的更高维、高无数维的世界。对几万年都无法解决一些最基础的纷争的蠢笨人类来说,这种“智能”多少可以提供一些反哺,有可能让我们过得不那么糟糕——即便是作为那“智能”的某种肉身奴隶。仅此而已。
3
更有甚者。历史的考察——如果我们不带浪漫的柔光镜片而是多少有些残忍地直视历史事实的话——其实早就告诉我们,真正的突破性的进展一向与模仿无关,相反,恰恰与终于能毅然放弃仿生的浪漫幻想的决绝程度高度相关。
实际上,机器/自动装置历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就是仿生的,包括但不限于模仿人类的生命体形态特征;另一种被称为“假体”,它打破了自然生命体形态特征的束缚,而完全服膺于“原理”——也就是科学的理论性建构——结果反而更符合自然运行的内在机制,甚至把这一机制,在抛弃肉体形态的束缚后,发挥到极致。
1738年,出身工匠世家的法国发明家雅克·德·沃康松一夜成名,他用机械装置,做出了一个能够惟妙惟肖地吹出优美旋律的真人大小的长笛手,震惊了巴黎;随后,他又推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一只机械鸭子,只要上一下发条,它就能拍打翅膀、啄食食物、喝水、嘎嘎叫,甚至能拉出一颗臭烘烘的东西。那一年沃康松才28岁,而事实上,早在十年前,他年仅18岁时,就发明出了可以端菜和擦桌子的“家务机器人”。后来,这只能拉屎的鸭子,连同他的机械长笛手、铃鼓手等,组成了一个极受欢迎、商业上很成功的巡回演出团,无论是在1742年英国伦敦的国王剧院,还是两年后在德国各地的亮相,都引起了热潮。事情按这么发展下去,沃康松就只是无数充满奇思妙想并且动手能力超强的能工巧匠之一,但他的天才远不止于此。沃康松没有陶醉于整个欧洲给予他的掌声,仅仅在德国巡演成功的第二年,1745年,他就搞出了一辈子最重要——虽然不是最有名——的发明:一台自动提花纺织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纺织机。正是在沃康松的纺织机的启发下,另一位法国发明家约瑟夫·玛丽·雅卡尔(Joseph Marie Jacquard)设计出了第一台自动织布机——雅卡尔织布机。
另一个例子。在达·芬奇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手稿中,有一份是专门研究鸟类飞行技能的,现在就被命名为《鸟类飞行手稿》。他在其中对鸟类如何在飞行中保持平衡、移动、掌握方向、俯冲和上升等做了大量研究,基于这些研究,他亲手制作了多个飞行器,并拿到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山上去试飞,可惜无一成功。1896年,当时英国物理学界的带头大哥、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后来(19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利勋爵(原名John William Strutt)公开宣布:“除了气球以外,我丝毫不相信其他任何飞行器。”瑞利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偏见,而是有其充足的物理学理由。他是研究气体密度的专家,还是惰性气体的发现者。按照当时延续自达·芬奇的对飞行器的仿生学构想,类似鸟类拍打翅膀的动作无论如何没法抵消机械本身的重量。可以说,如果囿于仿生学思路,瑞利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但仅仅7年后,莱特兄弟就造出了真正的飞机。关键是这两个美国人没有那么多“文化传统”上的束缚,他们最终抛开了鸟类的飞行原理,而把目光投向了引擎——由航空发动机提供的升力,是仿生学构想中的翅膀完全无法比拟的。
无论是沃康松还是莱特兄弟的例子,都令我们清晰地看到,一旦抛弃仿生的幻觉,一种建立在浪漫幻想之上的“奇技淫巧”可以多么迅速地——只需几年时间,转化为改变整个世界图景(以及我们对它的理解)的革命性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ChatGPT同样是此类充满仿生迷惑性的“奇技淫巧”,但它背后的真正“原理”,即基于超高维度(从数学上说,有多少参数,该模型就有多少维度)的大语言模型,只要抛开其仿生学束缚(一个“像真人一样”的对话者),其真正的生产性就可能呈指数级爆发。从历史经验看,很可能这种蜕变就像自动纺织机和飞机的横空出世一样——前者缓慢但不可阻遏地导向工业革命,后者则将人类送进了航空航天时代——需要的也不过只是几年时间而已。
4
而当我们能够打碎仿生学的窠臼,破开一片前所未知的广阔天地,反过来,我们也能对生物有机体的“模拟”性状有更根本更彻底的认知。
约翰·冯·诺伊曼在其未完成的遗作《计算机与人脑》中,对此做了一个堪称伟大的示范。这本小册子是冯·诺伊曼应耶鲁大学之邀,为他计划于1956年春季学期里举行的“西里曼讲座”而准备的手稿,可惜他1955年被诊断出骨癌,到1957年去世,讲座未能启动,手稿也没有最后完成。其时,冯·诺伊曼已经深度介入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对神经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冯·诺伊曼(右)与奥本海默(左),后面是由冯·诺伊曼主导设计和督造的早期计算机EDVAC
《计算机与人脑》粗看似乎是由两部分拼接而成的,第一部分是早期计算机的原理,包括模拟机和数字机,第二部分则是对神经系统及其功能的解析。其实冯·诺伊曼采用的这个有些生硬的结构,恰好符合前述马克思的名言——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里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为:对现代计算机原理的掌握,是理解神经系统以至人脑运作的钥匙。
可以说,在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设计思路确定之前,我们对人脑和神经系统的所有了解,都不过是基于解剖学的模拟性猜测。是计算机设计和运行过程中所使用的数字化“语言”,给予我们一种理解人脑和神经系统的全新视野——所以并不是“电脑”在模仿人脑,恰恰相反,是基于数字原理的计算机的成功,反哺了我们对人脑的研究。对此,冯·诺伊曼写道:
“神经脉冲可以在前述意义上被清楚地看作(二值)记号:没有脉冲代表一个值(例如,二进制数字0),而有脉冲则代表另一个值(例如,二进制数字1)。当然,这必须当作在特定轴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特定神经元的所有轴突)上发生的现象来理解,并且可能在特定时间内与其他事件相关。因此,它们可以被解释为起着特定逻辑作用的记号(二进制数字0或1)。
“如前所述,(出现在给定神经元的轴突上的)脉冲通常由撞击到该神经元细胞体上的其他脉冲触发。一般来说,这种触发是有条件的,即只有这种初级脉冲的某些组合和同步才能触发所涉的初级脉冲,所有其他的脉冲都不能引起这种激励。也就是说,神经元是一个接受并发出明确物理实体(脉冲)的器件。一旦它接收到某些组合和同步的脉冲,它就会被刺激发出一个自身的脉冲,否则它将不会发出脉冲。描述它会对哪些脉冲群作出响应的规则,同时也是支配它作为一个有源器件的规则。
“显然,这是对数字机器中器件功能的描述,同时它也描述了刻画数字器件的作用和功能的方式。因此,它证明我们最初的断言的合理性:即神经系统具有表观的数字特征。”
正如薛定谔以其基于量子物理学研究的“生命物理学”,大大拓宽了传统生物学的视野;冯·诺伊曼作为横跨数学、物理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全才”,同样以其对“基本原理”的洞察,否定了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对仿生的路径依赖,反其道而行之地将当时尚是初创阶段的计算机思想,特别是其逻辑和数学“语言”,用于神经生物学的描述与研究,这是真正的天才才具有的“通感”。
可惜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为今天哪怕是很前沿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科学家——比如杨立昆,比如盖瑞·马库斯——所真正理解。马库斯推崇的符号主义、杨立昆预言会淘汰大语言模型的所谓“世界模型”,本质上都不过是仿生学的当代数字化变种而已。

《计算机与人脑》
[美]约翰·冯·诺伊曼 著
商务印书馆 2021年9月版